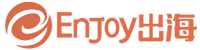核心内容
1、Balenciaga(巴黎世家)高价与抵制资本主义态度的矛盾来自于信息时代新兴阶层行动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2、达达主义具有批判精神,而“批判”正是新兴阶级这一矛盾人群的“消费需求”。
3、觉醒资本主义成为“铁律”,抵制文化盛行或是因为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缺乏公正性。
5月22日,在Dow Jones指数连续第七周连续暴跌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聚会——Balenciaga 2023年春季秀。这是Balenciaga在巴黎以外举行的首场秀,也是首次在NYSE,这一见证美国财富创造和毁灭的象征符号,举行的时装秀。
围绕Balenciaga创意总监Demna Gvasalia的争论不断,他将“世俗之物”标榜为时尚单品。New York Times表示,“他是一位天才,一个‘江湖骗子‘他是这一代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将NYSE设为秀场——不可否认,这个时机无可挑剔。
这是一场审视社会体制的时装秀,直指The Fetishization of Finance(金融的恋物癖)的诱惑与危险。开盘的钟声并非预示着当天的股市交易,而是旨在唤醒人们对于社会系统本身的反思。
AnOther杂志如此评价:“鉴于Gvasalia对世界末日舞台的喜爱,当我们徘徊在又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悬崖边缘,对于Balenciaga的最新一场时装秀,没有什么环境能与NYSE相媲美…… 该系列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扭曲’时尚”。
每一张被Gimp面具遮掩的模特面部背后,每一具被乳胶紧身衣裤包裹的身体背后,是社会精英为了追逐财富而扼杀个体身份的“匿名”行为。这种追逐让人窒息。
金钱是人类最大的“恋物癖”。Balenciaga认为,作为维持现代城市高速运转的血液,人们已经沦为工作的奴隶,“时尚”的奴隶。
衬衫搭配鳄鱼纹皮裙,褶裥波点连衣裙,以及腰部系带的背袋风衣,Garde Robe系列正在重新解读上世纪80年代热播美剧Working Girl中的都市新中产严肃的时尚风格。此外,宽肩剪裁与“小丑”靴(Clown Boots)的巨大廓形,以夸张的比例继续挑衅着传统审美。
NYSE交易大厅灯光昏暗,市场行情屏幕因出现故障而时常闪烁。Bloomberg UK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华尔街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更专注于Latex和BDSM,而不是Leveraged Buyouts和CMBS”。反乌托邦式的“末世”氛围,与被“扭曲”的“严肃”带来的视觉冲击,强化了人们对社会即将崩溃的恐惧。
事实上,Balenciaga向来不乏“宏大叙事”。从气候变化,名人文化,战争,到此次“迷恋旧世界的资本主义”,其设计概念总是基于这样一种视角,即“凌驾于世俗之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Gvasalia的作品却常常取材于世俗寻常之物。
作为本次Balenciaga x Adidas系列中最廉价的商品,NYSE T恤售价高达795美元。这个法国品牌提供了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视角,以嘲讽华尔街的拜金文化。然而,它却是该文化的主要受益者——Balenciaga就是资本主义本身。
对此,Bloomberg UK提出,区块链和DeFi正在颠覆传统金融系统。虽然具有反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声音或许会争辩,这场时装秀旨在隐喻“NYSE已经腐烂”但是,如果Balenciaga确实愿意抛弃旧世界及其金融系统,那么它早已经放弃华尔街而转向元宇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品牌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它刚刚宣布计划接受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
消费品牌在Web 3.0实验中呈现出的积极态度或许源于与Balenciaga x NYSE相同的一种价值主张,该主张基于对旧世界、旧体制的不信任与抵制。一些加密货币追随者也正是被类似的自由意志主义叙事深深吸引。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Web 3.0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西方大众所质疑的“旧体制”并不存在。
为什么Balenciaga能够包装并售卖“宏大叙事”而Lululemon曾主张的“抵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反思”却饱受诟病?为什么“挑衅美”和“蔑视世俗成功”深受消费者喜爱?为什么人们愿意以高昂价格为寻常之物支付费用?
文化战争:传统资本主义奉行循规蹈矩,波西米亚主义鼓励藐视惯例
早在20世纪,人们很容易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世界与波西米亚式的反文化生活方式进行本质区分。Bohemianism这一英文单词于19世纪中叶从法语引入,用以描述欧洲主要城市中艺术家、作家、记者、音乐人以及演员等文艺从业者非正统的生活方式。
1948年,即美苏冷战爆发的次年,The Beat Generation(亦作Beat Movement,即“垮掉的一代”)一词首度问世,用以形容一场最初基于纽约的文学和社会运动。“Beat”意指“疲倦”。美国经济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迎来空前繁荣,Beats抵制该时期滋生的物质主义并倡导精神追求,他们探索美国及东方宗教,是Bohemianism的践行者。二战阴影尚未散去,冷战核威慑带来的恐慌不期而至,Beats通过“脱离社会”和“反叛”以应对自己的处境。
时至60年代,Hippie文化运动的声势浩大。早期Hippies继承了Beats的反主流文化价值观。不过,Beats对政治主张缺乏热情,而Hippies则积极投身于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与先辈的“被动”应对之策截然不同。Hippies探索东方哲学和亚洲精神概念(Spiritual Concept),听迷幻音乐,使用大麻和致幻剂探索不一样的意识状态,倡导重新建立与自然的链接,并创建了自己的社区。
进入70/80年代,有趣的事情发生了。Bourgeois Ethos,即资产阶级精神,开始“反击”。1980年,Yuppie一词首次出现在芝加哥杂志,作为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Young Urban Professional),或向上层阶级流动的专业人士(Young Upwardly-Mobile Professional),的缩写。
新保守主义人士(Neoconservative)相信,资产阶级资本主义(Bourgeois Capitalism)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他们认为,Bohemians或许渴望宏伟的精神超越,但其最终实现的往往只是基于自我放纵的虚无主义;拒绝权威和习俗并不通往解放与幸福,相反,这只会导致自我毁灭。他们对反文化式的叛逆行为嗤之以鼻。
从早期的Bohemians,到Beats与Hippies,直至Yuppies,资本主义与反文化是一组相互对抗的概念,二者水火不容。事实上,早在Hippies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发起攻击之前,文化战争已经贯彻整个工业时代。在美国,Bourgeois代表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科技进步主义,代表精致的品味和优雅的举止;而Bohemians具有艺术气息,代表精神主义、反理性主义,代表冒险和返璞归真,代表原生粗旷的审美和基于自然主义的举止。
Bourgeois奉行务实主义,并且循规蹈矩。Bohemians(波希米亚人士)藐视惯例,具有自由精神。David Brooks在<Bobos in Paradise>一书中如此描述二者截然不同的属性,“Bourgeois捍卫传统和中产阶级道德。他们为公司工作,住在郊区,然后去教堂。与此同时,Bohemians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Hippies和Beats。Bohemians拥护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价值观,Bourgeois则是20世纪80年代有进取心的Yuppies“。
然而,这一局面被出生于90年代的Yuppies后裔——Bourgeois Bohème,简称布波族(Bobos),彻底改变。
布波族取代WASP成为信息时代精英:个体社会地位 = 资产净值x反物质主义态度
布波族的出现或是信息时代的文化后果——基于思想和知识的文化领先与基于资源与资本的经济成功同等重要。该时代将无形的信息世界与以金钱为计量单位的物质世界巧妙融合。因此,成功属于那些能够将“想法”与“情感”融入产品的人。正如Brooks所述,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一只脚涉足波西米亚式的创意世界,另一只脚涉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野心和世俗成功”。
60年代的硬核激进反文化分子认为,保留“真诚”自我的唯一出路是彻底拒绝成功——退出竞争。唯有撤退至远离城市的小社区,人与人才能真正重建连接。然而,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Résume Gods(简历神灵),这种乌托邦主义显然不切实际。毕竟,他们倾向于以世俗成功定义个体身份。此外,财富戳手可得,难以舍弃。
当美国婴儿潮一代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学位几乎没有带来经济回报或戏剧性的生活变化(编注:这一点与国内近两年毕业生所抱怨的情景极为相似——高等教育的边际收益正在迅速下降)。1976年,劳工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在<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一书指出,高等教育在市场上似乎没有回报。然而,信息时代的爆发让这一状况得到逆转。截至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70%,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毕业生的收入高出90%。大学学位的工资价值在15年内翻了一番——社会对智能资本(Intellectual)的奖励迅速增加,而对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却没有增加奖励。
社会阶级流动性增加使得旧社会让位于新社会。具有良好血统但是思维愚钝的美貌少年被饱读诗书、雄心勃勃、衣着毫不精致、并且“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聪明少年所取代。彼时,“新旧社会”以信息时代之处为分水岭。
在此之前,WASPs美国新教精英,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昂撒白人新教教徒),垄断了旧社会对精英身份的定义。Anglo-Saxon通常具有英国血统,不过社会学家在时常使用WASP以在广义上形容所有北欧或西北欧血统的新教美国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该人群主导着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1945年后,WASPs的支配地位受到批判,人们贬低他们为“建制”(Establishement)的一部分。
进入信息时代,受过教育的精英接管了旧体制下WASPs的大部分权利,在慷慨奖励其智能的新经济中蓬勃发展。然而,他们粉碎了精英文化,自己却成了精英。他们是反精英的新精英,他们是反建制的新建制。
这让他们面临经济富足的焦虑:如何向世界、不单向自己证明,即使已经攀爬至社会阶梯的顶端,他们仍然没有成为自己口口声声宣称蔑视的所有东西?如何确保自己不是WASP精英自大轻狂的复制品?如何在富裕和自尊(Self-Repect)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调和成功与灵性(Spirituality),如何调和他们“精英”的现有地位和其“平等主义”的宏大理想?
价值观与社会地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他们对贫富差距的扩大心存不安。他们钦佩艺术与智能,却发现自己被商业裹挟,或者至少,生活在创意与商业结合的奇特世界。
生活方式与消费品牌似乎为世俗成功与内在美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机会成本极低的解决方案。高端品牌采用巧妙的伪装,将价值主张作为概念加以包装。消费商品等同于消费“概念”本身。
布波族时常通过消费户外奢侈品牌取代户外冒险本身。为探险活动设计的登山靴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场景中度过——他们拥有的功能性商品总为比其实际使用场景更危险的活动而设计。这一趋势的结果之一便是,布波族的行动与理想之间往往存在差距,这一差距可能是冒险活动,也可能是道德信条或政治立场本身。
当Balenciaga售卖Garde Robe系列,其品牌溢价源于“反资本主义”立场。
当消费者为Balenciaga的昂贵商品支付费用,他们随即成为呼吁气候变化的环保人士,成为抵制“名人文化”的知识分子,成为反抗“战争”的和平卫士,成为蔑视“资本主义”旧世界旧制度的进步人士。
信息时代的精英努力权衡平等与特权,私人便利与社会责任,反叛与传统。行动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常常让他们显得有些自相矛盾,言行不一。
ProPublica一项基于最富有的0.001% 美国人税收记录的调查报告显示,2014至 2018年间,25位最富有的美国人总计赚得4010亿美元,缴纳136亿美元税款,仅占其收入的3.4%。然而,平均年收入45,000美元的单身工人支付的平均税率高达21%;一对年收入200,000美元且有一个孩子的已婚夫妇支付的税率为26%。
最富有的美国人和普通工人之间的税率差异能够归结为两个关键因素——富人享有的低税率主要受益于金融资产相关的极低税率以及慈善相关的税收减免。与美国普通员工获得标准薪水的收入形态不同,富裕阶级大多通过诸如股票等金融资产获得收入,这些资产通常以极低的税率征税。与之相对的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金融资产长期资本收益率高达20%。2018年,不包括投资的普通收入最高税率为37%,但从2013年到2018年,400名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平均税率为22%。
信息时代的新兴阶级——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缴纳的税率最低,其平均税费仅占收入的17%。这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多来自金融资产。富豪榜单中的前15位中有10位是亿万富翁,他们均在科技领域创造财富。2013年至2018年,Bill Gates平均年收入为28.5亿美元,平均缴纳的联邦所得税率为18.4%。Jeff Bezos在2007年和2011年没有缴税,而Elon Musk在2018年没有缴税。根据ProPublica,Mark Zuckerberg缴纳的平均联邦税率仅为13.7%。
当科技公司创始人及高管践行“一美元年薪”,他们同时花费巨大精力寻找社会系统中的漏洞以避免缴税。他们的财富价值随着公司估值增长而大幅增长,而这却并未计入纳税范畴。他们依靠此类财富以极低的利率向银行借款以维持高昂的生活开支,从而使其缴纳的税率远远低于消防员和教师。根据CNBC,美国财政部数据表明,最富有的美国人每年可能经过精心设计“合法”逃避了高达1630亿美元的所得税。
“一美元年薪”曾因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参与美国政府工作却不求政府回报的工业领袖及爱国人士采用而为人所知,如今,新兴阶层行动与理想的矛盾使之与初衷有所偏离。
当理想让位于象征性的仪式,当商品消费与生活方式替代文化抗议本身,新兴阶级或许已经向其内生性矛盾作出妥协。
这与The Beat Generation的演化路径如出一辙。历史学者Stephen Petrus如此定义初生代Beats,“他们对过度压抑、物质主义和墨守成规的社会不再抱有幻想,他们通过感官体验寻求精神再生”。然而,1957年至1960年,这一文化抗议变成了一种商品。Beatniks通过时尚使之得以呈现——宽松的毛衣、紧身衣、黑色紧身裤、贝雷帽和太阳镜风靡一时,该文化也通过空间得以呈现——咖啡馆和地窖夜总会。Petrus指出,这一时尚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传统异议的接受”。
正如David Brooks所述,若想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善待,你不仅要展示丰厚的收入,还必须作出一系列佯装,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一些反社会阶级的异常行为。这能显示这种世俗成功对你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你需要在谈话中嘲笑自己的成功,并且痛击Yuppies,借此表明自己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等于其资产净值乘以其反物质主义态度——二者任何一项为零都会让你失去声望。
Balenciaga能够成功以高价售卖“抵制资本主义”,而Lululemon发起的相同尝试却被指责言行不一,或是由于二者目标客群迥异。与定位中端、更为亲民的Lululemon不同,Balenciaga为信息时代的新兴精英阶层提供其宏大理想的象征性符号,Balenciaga的矛盾源自客群自身的矛盾。
除了新兴阶级,Balenciaga消费者中也不乏潮流玩家。值得注意的是,Cancel Culture(抵制文化)带来的社会氛围或能塑造消费者意识形态,从而影响消费决策。
由于布波族最早于90年代出现,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价值主张如今不再限于少数派。企业与个人社会责任曾经由布波族“拉动”,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并由消费者“推动”。
时至2010年代中期,Woke Capitalism这一概念,即觉醒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主流媒体并应用于旨在吸引千禧一代的营销活动。事实上,早在布波族诞生伊始,David Brooks便引入“Enlightened Capitalism”用以形容这样一种现象——商业体将利润与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消费者可以“拯救雨林,缓解全球变暖,培育美洲原住民价值观,支持家庭农场,传播世界和平,减少收入不平等”,所有这一切都能在世俗世界中实现。“过去人们认为,追求利润不可避免地会粉碎道德价值观。但现在,只要大量受过教育的民众愿意为社会责任支付溢价,正向价值观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
与美决裂:源自杜尚,Balenciaga通过世俗之物挑衅旧世界、旧系统
对布波族的剖析能够从消费端解读Balenciaga的商品为何能够契合目标客群的心理需求,但是Balenciaga的设计概念从何而来?
在《小众即大众,审丑入主流:「反抗精神」支撑的街头时尚为中国品牌带来哪些启示》一文中,元气资本曾提及Marcel Duchamp(马塞尔·杜尚)对包括Virgil Abloh以及Demna Gvasalia等街头时尚灵魂设计师产生的决定性影响。“Gvasalia甚至坦言,其审美的形成就是理解杜尚的过程”。
为什么从Off-White到Balenciaga,杜尚是品牌践行其价值主张的关键?
杜尚常被认作是实验艺术与达达主义的先驱。家庭文化氛围与父亲对其职业选择方面的宽容态度使杜尚对艺术习以为常,这对其日后打破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有着积极影响。
1912年,杜尚的画作<Nu Descendant Un Escalier N°2>在递交立体主义画展时被主办方拒绝,理由在于作品中除了立体主义,还存在未来主义特质。这成为杜尚生命中的转折点——杜尚决定放弃职业意义上的画家身份,不再依靠任何团体,投身于独立创作。1913年,杜尚退出画坛,在Sainte-Geneviève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专注于学术领域,研究数学和物理,开始艺术科学实验。在此期间,杜尚找到了新的艺术形式——现成品(Readymades)。
今天,设计“挪用”(Appropriation)便是“现成品”当代时尚界的延展。Martin Margiela挪用复古服装并制作复制版本;Helmut Lang的作品常挪用警察制服和其他功能性物件;Virgil Abloh称杜尚为“律师”,这位现成品先驱能为Abloh的一系列挪用辩护;Gvasalia的闪耀之处在于其对诸如“宜家袋”等世俗之物的挪用,以及原版和复刻版之间巨大的价格差距。
现成品不存在美,不存在丑,不具有任何美学性质。物件仍然是同一个物件,只是它被选中并作为艺术品得以呈现。与这种“取消艺术边界”的做法相似的是,在Balenciaga本季秀场中,Garde Robe系列是对Logo的反向解读,Gvasalia认为,没有Logo才是Logo未来的趋势,“时尚单品的魅力来自产品本身”。
自杜尚决定不再成为画家之际起,与美决裂,是其与传统艺术决裂的重要步骤,而现成品便是“质疑艺术”的工具。杜尚认为,艺术,以及对艺术的崇拜,是“不必要的”。1917年,杜尚以作品“Fountain”(泉),一个附有笔名R.Mutt的小便池,震惊艺术界。
事实上,晚年的杜尚不再激进,逐渐开始与世界和解。不过,“泉”正是凭借这种激进于2004年被500位著名艺术家和历史学家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品”。
达达艺术家有意激起观众的“震惊”,这种公开挑衅常常意味着破坏。艺术家在破坏旧审美的同时,也在破坏旧制度。人们普遍认为,颠覆传统资产阶级艺术形态的达达主义源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怖的负面反应。达达主义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理性和审美。这一反叛艺术流派通过“反艺术”与“反逻辑”宣扬反战立场并抵制资产阶级——通过破坏旧世界的审美以批判旧制度本身,这与Balenciaga不谋而合。
达达主义具有批判精神,而“批判”正是新兴阶级这一矛盾人群的“消费需求”,这解释了为什么Balenciaga通过承袭杜尚的艺术实验以挑衅旧世界、旧制度,从而满足消费者的“批判”需求。
「抵制文化」与「暴民正义」
如前文所述,道德消费需求的大众化普及催生了觉醒资本主义(亦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当Balenciaga售卖环保、反战、抵制物质主义等概念,觉醒资本主义为品牌贡献了巨额溢价。然而,这一趋势争议不断。
一方面,不少品牌为了迎合道德消费需求,常以最低的成本将道德形象最大化,“觉醒资本主义”由此成为一种营销方式,而非问题解决方案。The Atlantic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品牌倾向于发出低成本、高噪音的信号,以替代真正的改革,从而确保自己得以生存”。对此,Unilever首席执行官Alan Jope称之为“Woke-Washing”(觉醒洗涤)。事实上,企业在ESG方面的尝试常常面临“漂绿”的质疑。
另一方面,一些经济体将觉醒资本主义视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的罪魁祸首。该论断往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资本主义必须无情地把利润和股东利益置于首位,这是它的神圣职责。为了安抚利益相关者而追求可持续发展或社会性目标等崇高言论将致使企业牺牲利润并走向灭亡。
诚然,定位中低端的品牌在许诺ESG目标时,很可能意味着利润受到挤压。不过,作为定位高端的奢侈品牌,Balenciaga有较为广阔的提价空间,很难受到觉醒资本主义的负面经济影响。恰恰相反,由于“批判”态度已经成为Balenciaga的商品,品牌正是基于觉醒资本主义概念得以成长。
本文作者认为,在自由主义驱动经济发展的西方社会,政府干预能力弱化致使商业体与利益相关者矛盾恶化,而觉醒资本主义的意义便在于以社会自动调节机制应对这一矛盾。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取代缺席的政府功能。
权衡“利益”与“和谐”至关重要——以“利益”为单一导向的经济激进主义(Economic Radicalism)必然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而以“和谐”为单一目标的社会激进主义(Social Radicalism)将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进而导致经济瘫痪。然而,截至目前,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显然没有学会如何掌握觉醒的限度。Cancel Culture,即抵制文化,便是社会反应过激的例证。
由互联网主导的社会运动孕育极端主义,滋生暴力。从诸如#MeToo和#Black Lives Matter等女性及少数裔民权运动,到支持环保、宣扬平等等环境及社会责任价值主张,抵制文化为觉醒资本主义铸造了“铁律”。这种离散式的问责制使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活动的商业体与从业者置身于被社会驱逐的恐惧中。
为了努力适应大众支持社会正义事业的新世界,曾经建立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等资本主义原则之上的企业和机构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不得不作出让步——“进步”价值观(Progressive Values)由此成为一种强大的品牌工具,用以应对社会激进主义。机构当权者频繁表露引人注目的“进步”姿态——谴责种族主义,邀请女性进入董事会,解雇在互联网上引起众怒的低级别员工。
批评家对Mob Justice(暴民正义)发出警示,而活动人士则“沉醉”在自己“改变世界的力量”中,“我们拥有Twitter账户,我们能够对抗政府和企业巨头”。
西方的抵制文化将挑战政府、挑战体制视为英雄壮举。在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缺失能够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其对金融机构的信任缺失或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旨在通过独立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以实现去中心化的Web 3.0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成长。
人们对政府和体制的抵制愈演愈烈或是由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股市持续飙升,普通公民的薪资却停滞不前。根据EPI数据,自1979年以来,美国生产力与典型工人薪酬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1979年至2019年,美国生产力增长了59.7%,而普通工人的薪酬却仅上升15.8%。这意味着,工人提高生产力所带来的收益没有惠及生产者,而是主要流向了企业、股东,以及薪酬可观的高管。
在<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des Beaux-Arts:Critique de la modernité>一书中,Jean Clair用弑父杀子的Cronus比喻否定过去、把决裂当传统的先锋派艺术。自杜尚将小便池送上纽约的艺术展,“求新、求变、求怪、求惊人”的先锋艺术便开始让否定成为老生常谈,让反抗成为机械程序。
当批评成为修辞,当犯规成为仪式,抵抗艺术便失去了创造性,其本身也已成为僵化的产物。
如今,这种艺术已经成为Balenciaga的商业工具。在抵制文化盛行的社会背景下,“否定”即“进步”。
文章来源:元气资本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 Enjoy后台
Enjoy后台 登出
登出